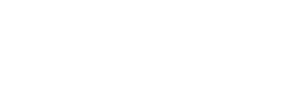相对于数字技术而言,“人肉”是低效、倒退和反技术的,但是当前却存在着人肉搜索、人肉评论、肉身翻墙和人肉代购等具身传播实践。除了从政策的角度来分析这些现象外,身体与传播技术的视角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消除人与技术二元对立的契机。身体将人与网络连接在一起,中介了人与网络的关系。从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视角出发,可以将具有物质性与文化特征的身体视为行动者,用“网络化身体”(networked body)这一概念讨论作为中介和非人的身体如何将人与互联网连接在一起。在此逻辑下,媒介不是人体的延伸,反过来人体成为媒介的延伸。通过经验研究发现,人的身体能够生产数据、成为网络的义体,因此可以作为技术系统的“补丁”存在。与此同时,物质性的身体又能够切断与网络的连接,作为破坏网络秩序的“病毒”存在。从身体这一混杂物的角度,可以发现人与网络技术的复杂关系,同时“网络化身体”也为如何从身体角度研究传播现象提供了新视角和方法。
2012年陈凯歌导演的电影《搜索》讲述了人肉搜索引发的悲剧。在中国现实情境中,人肉搜索引发的新闻事件屡见不鲜。这个概念的有趣之处在于用机器的逻辑来描述人的行为。网络时代的信息搜索主要由联网计算机通过算法获取,但是网络的数据还不足以成为博尔赫斯(1996)所说的包罗宇宙所有信息的“巴别图书馆”(世界之书)。所以线下的人体感官和大脑记忆提供和补充了网络所不具有的数据。中国最早的网络人肉搜索案例“铜须门事件”(2006)和“高跟鞋虐猫事件”(2006),都是通过网民对图片中人物和地点要素的人工识别获得线索发现事主。而更有名的恐怕是周正龙拍摄野生华南虎的事件(2007)中当支持者与反对者两方意见僵持不下时,一名网友提供了自己家客厅虎画的照片,补充了网络虎照数据的缺失。在这些事件中真实的人充当了图像、信息识别终端与数据库的功能,搜索者的身体被整合进了网络。
另一方面人肉搜索也指通过挖掘个人的现实痕迹与数字足迹(digital trace/footprint)(包括网络账号、平台实名身份、互联网协议地址、地理位置、网络图文发帖中的线索等),从而推断出“人肉”信息(包括真实身份、住址、工作、亲友和线下生活等),令其成为网络暴力的对象。这也把被搜索者的身体整合进了网络。因此,从以上两方面来看,与其把“人肉搜索”视作网络行为,不如说这是直指互联网所具身化的真人、真事和真实场景的实践。
类似的现象还出现在“人肉评论”“人肉代购”、快递、人工鉴黄、人工数据标注、“粉丝养号”、游戏代练(goldfarmer)等现象之中。在中国,“人肉”甚至成为网络中独树一帜的具身传播现象和技术实践逻辑。互联网滥觞时人们便期待,远距离电脑中介的传播隐去了交流者的身体,从而“灵魂”的相遇和沟通不再受身体所处时空羁绊。人们也畅想,机器之手能够取代大多数的人工劳动,使经济活动和信息传播更为畅通高效。但是在特定的情境中,我们看到相反的现象:不是网络媒介在替代人的身体功能,反而是人的身体在成为网络的一部分。或许麦克卢汉(2019)的那句“媒介是人的延伸”要颠倒过来:人是媒介的延伸。
相对于信息技术而言,“人肉”被认为是低效的、倒退的,甚至反现代化的,为什么当前中国仍有不少这种“倒退”,身体又是通过什么方式被连接在一起、成为网络的一部分?或者更一般地说,身体与网络技术之间存在何种关系,通过身体这一被传播研究所忽略的视角,可以发现网络媒介的什么新特征与构成方式?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本文将以身体视角重新观察中国互联网技术和网络社会的关系,强调人与物(技术物)之间流动的边界和联结状态,以及它们共同促成的异质网络关系。具体来说,这里将“人肉”所衍生的具身传播实践概念化为“网络化身体”(networked body),以理解其中身体实践、身体观念与传播技术的关系。借着这一概念化可以反思中国互联网技术系统的形成和运转逻辑。受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ANT)视角启发(Latour,2005; Law,1999),本研究将通过对网络代购和快递员的两个田野经验研究中的发现,讨论具体场景下围绕身体而塑造的行动者网络,以理解“网络化身体”的特征。
身体在传播研究中一直被忽视(刘海龙,2018)。近些年来,由于媒体技术的去蔽作用,肉身在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受到挑战,离身化的交流是否取代具身交流的问题成为新的焦点(拜厄姆,2020)。国内传播学界近年来开始讨论身体与传播的问题(刘海龙,2018;孙玮,2018、2020;芮必峰、孙爽,2020;杜丹,2020),但是由于观察视角不同,实际研究中所涉及的传播中的身体概念并不相同,导致混乱。
目前在传播中关于身体的讨论,有的直接用“身体”(body)或“肉身”(flesh),侧重身体的物质层面,或者文化层面。还有的用“具身”(embodiment)或“具身传播”(embodiment communication),这就更加复杂,既可理解为认知心理学主张的肉身在认知中具有重要影响,也可以反过来指那些技术与人的感官融合而形成的传播形式。后者就像唐·伊德(2012)所说的当技术处于海德格尔所说的“上手”状态时,使用者会忘记技术的存在,将“透明化”的外部工具当作我们身体的一部分自如地使用。当然,正如提出“媒介是人(身体)的延伸”的麦克卢汉很早就注意到的那样,这一表面上透明的延伸其实并不透明,媒介也改变了人的感觉方式。这开启了研究身体与媒介/传播的传统。
除了麦克卢汉(2019)提出的问题外,在身体与媒介/传播的话题之下,又发展起了众多新的取向。而且传播研究也未必亦步亦趋地拘泥于哲学或认知心理学中具身性的概念,完全可以在借鉴参考的基础上,基于本研究领域的问题意识重构身体的问题,从而为身体及具身性概念注入新的意义。
虽然身体未成为传播研究的中心议题,但是传播研究已经零星地涉及了身体问题,只是之前并未从身体的角度来理解这些成果。关于身体与传播研究的传统路径有两个。一是将身体视为符号和象征系统,如人际传播的非语言传播中对身体语言的研究[戈夫曼(2017)的研究也属于此类]。二是将身体作为文化和权力的展开与配置场所(place),比如人类学、社会学和文化研究里对身体的研究(毛斯,2003;福柯,1999;埃利亚斯,1998;布尔迪厄,2017)。前者将身体视作象征符号,忽视了身体的物质性,后者将身体视为症候和表征,所谓的传播,主要局限于展演和争夺,是表现形式而不是视角。
从目前涌现出来的研究路径来看,从将传播与身体结合在一起产生的传播领域的新问题至少有如下三个:一是在一定传播技术条件下,作为经验感官的身体会使人的生存方式发生什么变化(梅洛·庞蒂,2001;本雅明,2006;孙玮,2018)。二是在传播中将身体作为隐喻向世界投射(维柯,1997;莱考夫·约翰逊,2018)。三是作为传播的基础设施和条件的物质肉身会如何影响传播的方式与质量(彼得斯,2017、2020)。
本文主要是在第三个身体物质性的维度上使用身体概念。借助日常语言中的“人肉”概念,可以突显身体的物质维度。它的可感知性和实体界面既可能被网络征用为其终端,实现身体与网络的连接,同时也因为身体具有洛克所说的相互隔绝的特征(彼得斯,2017:119-129),从虚拟网络的操控中逃逸。身体的物质特性决定了人与网络之间关系边界的基础。这是探讨人与技术关系时常常被忽略的一个维度。
“网络化身体”展示了一种与互联网技术关联的另类方式,即,被整合进互联网技术运作体系的身体与具身传播。“网络化身体”是指被接入网络,成为网络延伸的身体。这种关联不完全等同于将互联网视作身体形象或者身体经验的具象化(Hine,2015)(Hine的观点强调互联网实践的社会文化意义是线下个体生活经验的延伸,它化身为人的视界和心灵之窗),也不同于将互联网界面视作身体物理和社会活动互相对应的映射(Farman,2012; Sheller& de Souza e Silva,2014)(Farman等人强调,互联网是联结身体实践与实体物理空间的社会空间,它们相互定义)。“网络化”的身体强调物质性层面,关注互联网技术运作逻辑与身体的物质性(即肉身)和传播的具身性(即身体在场)之间相互作用。身体作为人的基础设施与网络具有相同物质基础,可作为网络扩展硬件的一部分与网络连结。至少在目前状态下,许多网络信息的输入要依靠身体物理功能(手指运动、声音、行动轨迹等)。所以身体成为了人与网络可连接性的基础。
本文从行动者网络理论(ANT)视角出发,提出“网络化身体”意味着寻求另一种关于中国互联网技术系统的认识论。借此,我们可以转换思维讨论网络技术衍生的那些看似与技术相矛盾的身体观念和实践,以及我们对所谓技术社会影响的理解。ANT理论视角以拉图尔(Latour)、劳(Law)和卡龙(Callon)为代表人物,提倡任何通过制造差别而改变了事物状态的东西都可以被称为“行动者”(actants),它们包括人和非人的行动者(如观念、科技物和生物等)。拉图尔反对将行动者看作处于特定社会结构性位置以完成该位置预设功能的人,在功能主义看来这样的行动者(actors)扮演的角色是无差异的。他认为,社会(social)不是一种外在的结构性表征,而是一系列行动者相互关联的轨迹(trajectory),ANT所关注便是社会联合的过程(Latour,2005; Law,1999)。ANT用转译/翻译(translation)的方式来分析社会联合的过程,即,网络的生成(Callon,1984),转译分析强调行动者的异质性和网络生成的非决定性,跟随行动者所说所想,考察在实践过程之中哪些行动者被卷入、被赋予了特定形态,以及转义者和中介者的运作(吴莹、卢雨霞、陈家建、王一鸽;2008)。ANT思想旨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挑战人与物、自然与社会、技术与文化这些现代性思维建构的二元对立(Latour,1991、2005)。
基于ANT视角来看人与技术物的互动关系,除了关注传统的作为行动者的“思想人”外,物质身体本身也可以被看作行动者,这样身体便不是技术实践之外的另一类问题。甚至按照梅洛-庞蒂(2001)的观点,身体是比思想更基础的人的存在方式与世界间的媒介,因此关注人与技术的关系就不仅仅要考虑符号与文化层面,同时首先要关注物质性身体与技术的关系。
“网络化身体”是围绕互联网技术而促动(enacted)和展演(performed)所形成的社会联结的一部分。人的身体成为互联网技术系统的一个部分,与其他的技术物相互塑造。行动者网络及其代表的科技研究视角与强调媒介社会学等强调媒介物的文化属性的取向不谋而合,后者同样用于摆脱功能主义传统(戴宇辰,2019)。“系统”概念除了与结构功能主义取向相伴,技术社会学和媒介社会学也进行“技术系统”分析(正如上文的讨论)。而正是“网络”和“系统”的概念化分歧,使得ANT受到媒介学者如西尔弗斯通(Silverstone)的批评(戴宇辰,2019)。本文无意进一步加深“网络”与“系统”概念之辨,故文中也包含技术网络和技术系统两种名称。重点在于本文采纳ANT的分析视角,强调技术物在具体社会场景下生成的关系性和展演性是非决定论的(Law,1999),提倡用“生成联结”的方式理解局部(local)和整体(global)之间的辩证关系(Latour,2005),这样的思维转换使得我们无需纠结于互联网技术系统整体性和单一要素之间的界线问题。“网络化”身体,又或者说身体的“网络化”,可能出于多元行动者(actants)关系下,促进既有关系的分化,也可能是新联结的生成,身体所扮演的角色转换随网络关系而变动。
正如ANT理论所主张的,“社会”“网络”“权力”都是结果而不是原因,要考察个体构成网络的动态运动、替换、变形、转译、征召过程。同样,网络化身体概念也可以让我们放弃之前刻板的“网络”概念,打破人与网络的二分法,从物质身体层面重新考察身体(人)是如何运动、流动、变形、转译、征召,甚至与网络相互替换的,如何与数字硬件和系统一起重新组合成新系统的。这就像生产线上的工人与机器人,他们在技术网络面前,是完全可以相互替换的。当工人的成本低于机器,就会使用工人,反之,当机器的成本低于工人,人就会被机器替代。反讽的是,资本最忠实地实践了ANT所倡导的生命与无生命的行动者完全一视同仁的原则。
由于ANT所说的网络是个动态的过程,身体在网络中的地位与功能也不是一成不变,甚至身体是否成为网络的一部分也是流动的。例如,代购的身体就动态地与网络连通或者断开。为了向买家展示商品可靠性时,可以通过位置信息、直播的方式与网络连接,但是通过海关的时候又会切断与网络的关系,伪装成普通访客。所以在考察身体(人)与网络(技术)的关系时,必须结合具体的网络、情境与实践方才能够理解二者的关系。
网络化身体类似德勒兹和加塔利所说的无器官的身体(body without organs)[也有学者将其理解为无组织的身体(body without organization)(霍兰德,2013/2016:105)](Deleuze & Guattari,1987/2016;1977/2009:8-13),必须打破原有的身-心二元论或者物-人的二元论和刻板印象,重新想象身体。当然,和德勒兹不同,这里谈论的不是欲望的重新结构(Deleuze & Guattari,1977/2009),而是网络的重新结构。不过正如拉图尔(Latour,2005)所承认的那样,ANT理论中的网络概念接近于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块茎”(rhizome)概念,是在无固定方向的横向蔓延中形成的。从德勒兹的意义上说,身体与其他行动者具有同等的自由与流动性。这就打破了结构与能动非此即彼的二元困境,网络的形成并不完全是主观行动的产物,同时也不完全是由结构决定的,物质性的身体由于其特殊性,既要服从物的网络化规则,同时又受到行动主体的支配连接或者切断与网络的关系。
网络化身体概念试图从物质性身体的角度重新理解人与技术的关系。本文选取其中“补丁”与“病毒”两种视角进行阐述。这两个概念来自计算机安全领域,从字面含义可以看出这是从网络系统的视角而非人类的视角进行的建构。它旨在说明互联网技术系统的构建并未脱离肉身实践和身体观念的影响,互联网将身体整合在其中,“网络化身体”在其中同时扮演着修补和对抗现代互联网技术和制度漏洞的“补丁”和“病毒”的角色。与制度化的媒介组织相似,身体实践适应互联网技术系统隐含的身体管理和节点控制规则,利用与网络连接或者切断的机会,建立不同的身体-数字网络。它们蕴涵着方向相反的力量:一种补充和强化技术既有的功能设定,另一种旨在对抗和破坏现行技术系统。当然,网络化身体的状态并非仅仅局限于这两种,这两种网络化身体类型及其功能并非简单排斥,在具体的个体身上还可能重叠和融合。
本文用代购和快递的经验材料分析来讨论这两种“网络化身体”。关于代购的观察来自谢卓潇(Xie,2019)的博士论文,包括2016—2019年对香港代购产业开展的实地和线上观察及40个正式访谈。她在2016—2017年开展了8个月的参与式观察,每周跟随代购者往返香港和内地,观察采购、过关、物流和销售等一系列行为,此后每年进行一个月以上的跟踪调查。关于快递的经验材料来自于束开荣(2021)的博士论文,他于2020年在安徽合肥使用参与式观察和访谈的方法,以外卖骑手的身份体验了三个月的送餐快递工作,并就快递过程中的人与技术网络的关系进行了深度访谈。
需要说明的是,这两个学位论文研究的问题和侧重点与本文所讨论的并不完全相同,但是这两个研究中积累的部分田野观察笔记为本研究的再阐释提供了原始素材。本文的结论独立于上述两个研究的结论。
“代购”行为在当前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并不罕见,跑腿代购、平台海淘集运、海外买手或者跨境采购都泛属此类交易。简单地说,代购是一种“中间商”交易,短途跑腿帮忙取货送货,跨境代购甚至形成长期交易网络。例如,香港代购在内地便形成了一定规模。2018年时在网络上搜索“代购”,淘宝上有252,441个店铺以“海外代购”为关键词;微博上有7,856,600个与“代购”有关的账号,600,972个与“香港代购”有关的账号。其中,有不少账号包含“人肉代购”的标签。“人肉”代购服务一般指的是“亲身”采购、“现场”选货、“肉身”携带商品过境。香港代购尤其强调在香港开展“人肉”代购的优势。“港代”的这一营销卖点不难理解:香港在销售品类和价格上有优势,又毗邻内地,代购者可以代替客户“在”香港选购全球商品,这种“海淘”甚至比亲自前往更为高效省钱。不同货品从其他国际市场转运至香港,分销到大大小小的供应者手上(例如,商场专柜、折扣商品连锁店、药房、针对代购的批发商),从香港流通到内地最快可以当日完成。
为了实现香港代购的优势,“人肉”扮演了整个香港—内地代购网络的重要“补丁”。据政府报告统计,2018年香港到内地的三大关口罗湖、深圳湾、落马洲的通关人数分别达到85,115,000、44,288,000和28,626,000人。[1]这巨量的流动人口除了游客,还有不少持两地身份的居民、留学生、导游和跨境通勤者作为代购活跃在关口。有兼职代购定期帮客户“人肉”采购,或帮自己做代购的亲友“人肉”搬运货品过境,也有许多专职香港代购,亲自到香港的专柜、折扣店和批发店采买、“人肉”搬货过海关。当货物价值大大超过海关限额或者代购者自身入境次数受限时,他们也会雇佣跨境通勤者、货车司机或水货客,借此完成“人肉”过关。为了高效地完成跨境物流,打通香港—内地采购的“最后一公里”,口岸附近围绕代购服务形成了许多集中的批发、零售和仓储据点。例如,天水围和上水地区有大大小小近百个商铺为“人肉”代购提供“一条龙”服务,热门产品基本可以一处买全,销售人员和代购批发商甚至为代购提供可一键转发的实时广告。完成一次跨境代购最快仅用两三个小时。通过上述观察可见,基于个人采购和物流之间的模糊性,将个人身体连接起来,构成了地下物流网络的一部分,参与了技术网络的运行。“人肉”代购网络化整为零,逃避监管,将行动者网络的流动性与灵活性发挥得淋漓尽致。代购者及其他参与者的肉身在代购活动中通过运动、变化和转译,也催生了更为复杂的网络关系。
然而,“人肉”代购并不能独立于互联网存在,代购网络的建立,除了身体的移动外,更重要的是要让消费者相信和见到商品(代购者身体)的移动轨迹。随意翻阅其中的“人肉代购”账号,可以看到许多鲜活的个人形象,他们比一般社交媒体用户发帖更频繁,每天少则数十条,多则近百条。这些人的代购账号几乎都留有确切的身份信息,以及具体的地理位置定位。为了证明“人肉代购”的真实性,代购者在网络上贴出了包含自己身份证、通行证和通行签注部分信息的照片,香港商场店铺前的拍照,购物过程的工作照和小视频,以及日常生活的留痕(例如,自拍、餐厅照片、清点货物、试用护肤品、出入关口、专柜商品特写、购物成果展示,等等)。在一些极端条件下,代购者还会分享自己的地理位置及移动轨迹,甚至会在购买过程中直接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与买家沟通,确认商品的品牌与型号。通过将自己的身体的数据和信息与网络连接,通过身体的感知数据与客观位置数据,补充网络缺失的信息,增加信任,减少交易成本。
追随人肉代购从内地到香港采购的轨迹我们会发现,这种看似简单的互联网跨地域商品流动囊括了人和非人的行动者(消费者、代购者的身体、境外商品、售货员、货物供应商、海关、交通工具、货币找换、物流技术、移动通讯服务)。身体在其中位于中枢。原因在于身体具有生产性,它可连接、可数据化、可监控、可计算。今天的网络系统的界面基本是以身体为参照设计,目的是让终端成为身体的延伸。在与网络连接之后,通过转译,网络将身体的感知和相关状态数据化,最终让身体成为网络的延伸,感知和搜集网络无法生产的信息。在这个过程中,身体与网络界面之间的转译至关重要,转译作为一种可追踪的连接方式,将不同的行动者连接在一起。
如果说代购的案例中行动者在连接网络时还具有一定的自主性的话,那么在送餐的快递骑手那里,身体的连接与位置数据生产则是他们从业的基本前提。骑手必须具备能够通过GPS定位、蓝牙等记录身体轨迹的智能手机才能从业,并且为了保证在工作过程中不断开连接,电动车的电池能够给智能手机供电(充电宝会妨碍骑手行动)。智能手机作为骑手与网络的接口,必须通过手机架与作为骑手身体延伸的电动车(含电池)连接在一起,从而完成网络对身体的收编。骑手在移动过程中,必须随时关注手机抢单,手机架就成为兼顾APP操作与驾驭安全的重要设备。这种“车机一体”装置成为身体与网络连接的界面。
接入网络的骑手身体源源不断地生产位置数据与行动轨迹数据、签到信息(自我报告)、订单完成情况信息,成为网络“补丁”,提供网络不具有的数据。这些信息对网络至关重要,平台会反过来对其进行监控。例如,刷机的智能手机可以伪造地理信息,因此平台如果自动检测到骑手的手机越狱,就会限制骑手接单或者短暂封号令其整改。另一个平台无法控制的是提前点送达(“提点”)。这个签到功能主要依靠骑手自我报告,被平台严令禁止,并通过位置信息和订户确认加以交叉检验。如果被检测到,配送站点和骑手都会受到严厉征罚。为防止误操作,很多骑手会把平台骑手APP界面中的“送达”按钮由触摸点击确认改为滑动手势确认。
平台之所以强调身体数据的准确性,是因为系统会根据骑手身体生产的这些数据,计算出预计送达时间(ETA)、热力图等,结合派单算法,反过来对身体的移动轨迹进行严格规训。2020年引起社会热议的《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描述的快递骑手的困境正是他们的身体成为网络“代臂”后,人也被一并作为物质零件被剥夺基本权利的后果。可是讽刺的是,正是这些网络化身体作为系统“补丁”生产的数据强化了“数字泰勒工作制”,人被彻底抽象为物质身体,成为网络中可与其他物质相替换的组成部分。在今日劳动力成本不高的条件下,大量快递、网约车司机、人工客服(语音的或者在线的)、播音员、生产线工人、数据标记员、网络审核员、网评员、游戏代练等职业均处于这一状态。
从计算机系统的角度来说,补丁指的是对于大型软件系统(如桌面操作系统)在使用过程中暴露的问题(一般由黑客或病毒设计者发现)而发布的解决问题的小程序。本文的“补丁”概念与其原始意义并不完全一致,这个隐喻借用了弥补系统缺陷的意象,强调身体被收编为网络或平台的一部分。人发明了工具和技术,但反过来人及身体却模仿技术乃至成为技术的一部分,这种麦克卢汉似的预言看似奇幻,在历史上却屡见不鲜。彼得斯(2017)就曾发现,19世纪末当电报、电话普及之后,通灵术重新兴盛,灵媒将自己身体想像成电信系统,并模仿其沟通机制。作为人类最根本的“基础设施”,身体的可连接、可数据化、可监控和可计算等特征是其成为网络补丁的前提条件。它的数据生产能力已经成为平台资本主义的重要生产力(Srnicek,2017)。同样地对于今日的社会治理来说,数据越来越成为一种元资本。在新冠疫情的防控过程中,以健康码为代表的系统已经将网络化身体扩展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正如基特勒所说,只有那些被整合进网络或者可开关(switchable)的人和物,才可以被视为是存在的(彼得斯,2020:31)。要成为网络硬件的一部分,必须与集成电路具有相同的机制,可在连接与闭合状态中自如地切换。我们可以在身体与网络中发现同样机制。
身体与网络连接的方式并非只有连接这一种形态,身体物质性的一面赋予了它与数码物不同的特征,即它可以断开与网络的连接,成为一个不被系统识别,甚至破坏既有秩序的“病毒”。这里的“病毒”概念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病毒,而是隐喻性的计算机病毒。
彭兰(2019)在讨论互联网法则时,也提到连接与反连接的法则。不过她是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层面讨论这个问题,强调的是人主观体验的倦怠与压迫感、过度连接的压力导致的反连接。本文讨论的反连接(断开)则纯粹是从物质和技术层面的操作,不是社会性的;它从后人类的网络视角看待人与技术的关系,而不是以人的主观感受为中心看待人与技术的关系。同时,关系层面上的反连接未必一定以物质层面的切断为前提,只要发挥能动性和自制力即可完成。而物质层面的反连接则需要具备一定硬件和政策条件,有时个体更难以操控(比如健康码)。
今天各种网络已经深度介入到社会生活,越来越接近德勒兹所说的“控制社会”(the societies of control),机器控制着访问与接入的权力(德勒兹,2001:203- 208)。但是物质的身体却能在特定条件下夺回机器的控制权力。身体之所以成为网络的“病毒”,是因为身体兼具连接与非连接的模糊性,当它向网络敞开时,呈现出可连接、可数据化、可监控和可计算等特征,但是当它重新恢复自己独立于网络的物质存在状态时,便能够切断网络的连接,伪装成其他存在,身体感觉与行动无法完全被数据化和网络化,突破网络与系统的规则限制,以隐形的方式重新进入网络,颠覆其秩序。与前面补丁的逻辑一样,网络技术的基础设施、组织制度和软件设置(例如包括网络协议、制度、终端、软件、物流和支付应用)是一个整体,在这个体系里身体和其他技术物是等价的,因此身体利用其模糊性转变成其他物,或者变得隐形。
信息在物质世界中不可见,可见的只是其载体。但是在信息网络的世界中,逻辑被颠倒过来,可见的变得不可见,物变得隐形,作为物质的身体一旦不向系统提供数据,便可以逃逸数字网络的识别与监控。
身体暂时从网络中断开,并不意味着身体永久脱离网络。它会重新建立起新的网络,同时也会在适当的时候会按照有利于行动者的方式将现实转译为数据,重新接入网络。这一点在下面讨论的代购与送餐快递中经常可以看到。通过这种“盗猎”的方式,行动者拒绝向官方网络分享自己的身体位置数据和移动数据。但这并不意味着身体成为孤立的原子,在重新接入原来网络之前,它会以新的方式建立起新的网络或接入另一个网络。正如ANT理论所预测的那样,网络永远是在动态中蔓延、生成,而不是固定不变的。
我们仍以代购和快递为例来讨论这一类型。代购这一灰色地带与个体电商、广告推广和零售中间商在非正规跨境交易市场中共生,对一些品牌的淘宝官方商店、大型跨境电商和大陆实体零售商产生一定的冲击,成为“病毒”般的存在。对于内地专柜和电商代购入侵内地消费者细分市场,利用价格优势抢走专柜和电商部分客源;对于香港或者其他地区的市场来说,代购组团囤货,导致专柜某一产品迅速脱销,对当地和跨区域市场也产生影响。为此,代购活动也受到一些反制,例如,香港2013年起实施的奶粉限购令和内地2019年的电商法的实施。
代购对不同技术系统的“病毒式”入侵,很大程度基于代购参与者个体灵活的网络连接与反连接机制和身体“分布式”的存在。在特定时刻,代购经由其他行动者适时征召和聚集,与网络中不同的行动者关联,在完成行动之后,他们可以断联,继续“分布式”地存在于网络之中。如前文所描述,香港代购网络内部包含的代购批发者、个体代购和水客之间跨境“人肉”搬货,以及两地边境仓储,便是利用“分布式”身体规避管控。更大范围看,代购分布全球,有亚洲代购圈,欧洲、澳洲、美洲代购圈,都体现了这一点。不少代购者互为销售代理,代购者本地采购,再利用跨境物流倒买倒卖,从不同方向调动商品往中国市场流动,无形中入侵着区域市场边界。
代购身体线上—线下的分布和聚集转换,成为他们生成行动者网络,入侵其他网络的手段。这在购物节语境下体现得尤为明显。一般来说,香港的崇光百货的“感恩周”或者美国的“黑色星期五”圣诞促销期间,代购的网络发帖和信息曝光程度远超过平时。从节前预热到购物节,微博、微信和小红书等平台会增加大量代购的“直播”贴。许多代购晒出现场排队和选货的场景,也有代购发帖组建临时群找人团购和拼单,招代理或者承接他人的代购代理业务。代购之间也会相互帮助排队、组团拼单,争取买到更多折扣商品。除了参加购物节采购,代购者也会利用如淘宝“双十一”和其他电商的购物节等消费时机,联合起来盗猎电商购物节资源,暗中与内地电商系统对抗。许多代购在同一时期展开与电商相似的促销手段,模仿“双十一”的折扣抽奖活动。代购们同时也制造一些图文和视频迷因嘲讽内地电商购物节的虚假宣传,对比代购的日常低价天猫商城的虚假促销,对比海淘正品和淘宝假货,以此塑造海外代购和内地购物网站的差异形象,阻止客户参与电商购物节。
网络连接与反连接机制和身体分布的可变性也成为代购自我保护的手段。201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正式生效之后,网络经营中的身份实名和交易税务管控变得更严。微信和微博里的代购者们纷纷改名,原先的“XX靠谱香港人肉代购”变成了“XX小买手”或者“XX买买买”,人们社交媒体中具体身份认证信息也逐渐被删,或者模糊处理。自拍和私人生活表露的帖子减少,或者变成了“仅好友可见”。许多代购者网络中曾公开可见的身体数据消失了。但是新的网络又通过人际网络、微信群、QQ群、贴吧、小红书等社交媒体平台重新建立起来。在平台上隐形的身体又通过新的连接与买家建立起新的网络。
由上述可见,代购本身就是对参与者身体连接性和可断开性的应用。代购“分布式”的身体负载体量小,因此在商品进出口网络中是隐形的,具备了化整为零的可能。同时游客的身体与水客的身体在表面上完全一样,水客的身体切断了和物流网络的连接之后,便成了游客的身体,在海关的网络中也很难被简单数据化并加以甄别(走私网络会征招没有案底的人充当水客,就如电影《过春天》中表现的那样)。于是代购利用身体的模糊性和可断开性,成为监管中难以察觉的“病毒”,破坏网络秩序。正如计算机中的病毒一样,作为“病毒”的身体及其实践也具有很强的复制性,使网络系统的部分规则失效。
外卖骑手尽管在大部分时间都是网络的补丁,但是面对平台的不断压榨,他们也会采取本地的措施进行抗争,身体从网络中的断开就是其中常用的一种。
在《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这篇报道中,提到了所谓的“时间失踪”,即上述外卖骑手所说的系统“压时间”或“吃时间”的现象。在《人物》的这篇采访中,“有骑手在2016年至2019年,曾三次接到美团平台‘加速’的通知:2016年,3公里送餐距离的最长时限是1小时,2017年变成了45分钟,2018年,又缩短了7分钟。2019年,中国全行业外卖订单单均配送时长比3年前减少了10分钟”。[2]晚点送达会被扣钱并影响个人的评级,因此一些骑手在紧急情况下就会断开身体的位置数据或提供虚假数据。虚拟定位使得安装在手机中的位置媒介与平台对骑手的实时位置追踪之间失去联系,平台无法根据骑手的实时位置来评估他们对整个订单各个环节的完成情况。
前面提到的利用刷机越狱制造虚拟定位逃过系统监控,这是一种极端做法,随着监管的严格,已经越来越难实现。但是提前点送达按扭(“提点”)本身仍是骑手尝试与技术地理进行策略抵抗的一种方式。他们在挂单过满或者送单过程中遭遇状况时,会利用提前点送达来缓解由时间评估带来的超时风险和评级下降,具体来说是在特定时段打开手机的“飞行模式”(即关闭智能手机的位置媒介——蓝牙),临时切断与网络的连接,这样系统无法对比身体位置信息与送达目的地的信息。等到送到后再重新连接,逃过平台的监管。
除此之外,外卖商家刷单则是商家利用骑手身体数据与物质商品的可断开性进行的违规操作。找熟人下单的方式将订单发出,当骑手接单到店后,会被告知没有商品需要配送,这时骑手只需要驾驶空车从门店跑到订单的目的地(通常距离很近),然后点击界面中的“送达”按钮即可获得平台或者第三方劳务公司发放给骑手的订单劳务费。甚至有的时候骑手为了给自己刷数据冲业绩,也会自己下单自己抢。
不过上述物理断开的操作都是比较极端的情况,更常见的还是从机器的角度思考问题,利用系统的漏洞,通过身体兼具连接与断开的潜力进行的虚假连接或虚假断开的行为。例如,一些滴滴司机发现,如果一天跑十几个小时,平台就会派发各种小单。但是如果干一段滴滴,再去其他平台干,让滴滴停一两天,再干的时候就会接到比较大的单。因为大数据监控到司机有退出的趋势,就会用更好的活留住他。外卖骑手也在从网络的视角重新规划身体的轨迹数据,以取得较好的派单。例如,研究系统的热力图,寻找好的“常驻”地。因为骑手可以选择自己的工作模式是“常驻”还是“同城工作模式”,选择好的常驻地则会得到更多周边的运单。同样他们发现,如果自己的行动轨迹只是一条直线,系统就会认为自己经常跑一条线,容易没单。而跑单路线越花,说明骑手对这个地方越熟悉,后台就会把各个地方的单派给你,就会单多又顺路。
因为身体的物质性,能够独立于网络存在,切断连接,逃避网络监控,以新的身份重新连接,所以它成为人重新获得自主性的重要条件。韩炳哲(2019)认为社交媒体和数据监控使社会变得越来越透明,人的行为容易被操控。非连接以及物的不透明性则构成了对透明性的反抗。在现代科学思维占主导的时代,物曾一度也被认为已经被完全认识,对人已经完全透明。但是物向本体论认为科学并不是物的实在,我们对物的知觉与使用并不会穷尽物的实在,无法简单地还原(哈曼,2018:78)。因此物对于我们来说始终具有神秘性(海德格尔,2016)。作为物的身体也具有不透明性,无法被网络完全揭示。
虽然身体有不透明的一面,不过在无孔不入的技术面前,身体正在不可逆地被透明化。从手机泄露的运动轨迹、个人身份,应用程序秘密调用话筒、摄像头搜集个人信息,再到越来越强大的摄像头加人工智能图像识别技术构成的“天眼”,在网络中缺乏保护的个人信息泄露等,个人身份信息已经成为致命武器。例如,在香港修例风波中透明性成为攻防焦点,实施暴力者通过头盔、眼罩切断身体与网络的连接,反过来,暴力示威者通过在网上“起底”(人肉搜索)警察及家属个人信息,达到威胁恐吓的目的。[3]而正在开发中的“脑机接口”将使得人与技术的关系密不可分,切断与网络的连接的成本变得越来越高。
综上所述,网络化身体与两类“人肉”具身实践至少对应两种语境,即强化或破坏既有功能的语境。无论是哪一种语境,都突显了身体物质性的重要决定作用,而不是导向相反“虚拟化”和“去身体化”过程。身体与互联网技术的组合,从行动者网络的观点来看,通过数据化的转译过程,身体的物质属性和社会态只有纳入到一系列与技术物、信息、观察者、技术规制者、消费者、物流等组合情境中,方能理解那些看似与技术相矛盾的身体观念和实践。与此同时,“网络化”的身体受到技术逻辑的规约,也强化了技术逻辑的生成,身体被当成技术网络的“零部件”或者说技术的直接作用对象。这种现象有两种内涵:其一,它预示着技术对人身体的异化。其二,技术和人肉的互相利用和消减也体现了互联网技术集合在运转过程中的自反性。网络化身体并非去除对能动性(agency)问题的关照,而是把人和物的能动性视为同等重要的影响因素(Mol,2003),认识到在一系列的技术安排下身体或技术物所具有的有限能动性(limitedagency)。
简单而言,网络化身体指的是接入网络,成为网络延伸,与网络融合为一体的身体。网络征召身体,是因为身体能够为网络采集数据,成为其物质性终端(“代臂”)。当然,肉身的物质性在当下又成为其断开网络连接,摆脱其操控,成为秩序破坏者的前提。因此,身体与网络在“网络化身体”的概念下相互影响,互相建构,身体不再是自足的肉体,而具有了网络的特征,同时网络也具有了梅洛-庞蒂所说的“世界之肉”的特征,二者一起构成了更大的网络,这就打破了身体与网络、人与技术的二元对立。上面所讨论的“补丁”与“病毒”只是网络化身体的两个典型,并不足以概括网络化身体的全部特征。本文只是以此为例探讨这一概念的解释力。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疫情蔓延之时,网络技术成了各个层面实现信息流动、物资流通和人口移动的手段。普通民众、医生、专家、记者、政府机构人员、家庭、社区、市场、物理空间、病毒、野生动物、食物、药物、医疗用具、医学和信息传播技术,彼此关联在举国抗击疫情的行动网络中。网络化身体频频浮现:基于“人肉”调度的救灾物流,视频会议和课程直播的常规化,二维码化的身体调控,数据化的疾病身体,等等。身体的网络化和传播的具身化在不同时刻影响着疫情控制的进展。网络化身体概念也为进一步理解身体、网络以及人与技术的关系三个问题提供了启发。
首先,在前面提到的关于身体的几个传播学的研究路径中,存在着对于身体的不同定义,有文化取向、符号取向,也有物质取向;有侧重感官、心理的,也有侧重实体的。但是正如梅洛-庞蒂早就观察到的,身体的暧昧性本身就是其不可忽视和充满魅力的源泉。讨论身体的“网络化”,也意味着关注联结的异质性和不确定性。连接与非连接在于身体的模糊性,身体和网络的连接和非连接是液态的,这种液态特征缘于身体既是物质的也是非物质的特性(梅洛·庞蒂,2001)。人的存在方式依托于以身体为媒介投射和朝向世界,具身性存在突破了身心二元和身体的物性和感知能力的对立(Csordas,2011)。连接所折射的身体技术政治意味着身体是生产性权力关系的作用对象(福柯,2011),身体是社会惯习的具体化和承载方式(布尔迪厄,2017),然而连接与非连接存在的自反性身体运作,意味着身体是可以承担异质性认识论的表征,否定了单一的话语和对现实的认定(Mol,2003)。ANT提出的异质性行动者和网络组成,其本体论和认识论思想也呼应了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块茎(rhizome)和装置/集合(assemblage)思想(Deleuze & Guattari,1987/2016)。
在网络化身体的讨论中,可以发现身体既具有生产数据的能力,同时又具有物所特有的中介性和不透明性,打破了物质与信息之间的二元对立,产生出丰富的实践。或者我们可以借由身体的视角,超越关于技术属于物质还是文化的争论,更着眼于身体与技术的界面,关于如何使用身体的技艺及其实践。对于网络化身体的讨论便将其关注重点从人的身上转移到了身体技艺上。
其次,网络化身体作为人和物联结的新特征,提出了思考“网络化”如何作为媒介技术的社会影响的新视角。除了行动者网络理论外,卡斯特网络社会(networksociety)理论中对信息网络也进行过讨论。卡斯特强调,网络将全球的人与资源联系在一起,这一技术结构重塑了社会结构,成为了社会变迁的核心动力。按他的观点,网络化是信息传播技术的核心特征,因而当前的社会的经济、组织和文化交往都体现了这一转变(卡斯特,2000/2003)。卡斯特把技术和人放置在一起讨论,网络社会理论中也包含了“技术就是社会”的隐喻。然而,他的理论在分析层面仍将网络技术视为与人二分的工具,也似乎主要关照“集体的人”——作为社会构成的部分。结果,网络社会理论难以描绘微观层面的“网络化”如何发生、行动者如何关联、关联的性质、关系的逆转。拉图尔对宏观社会理论“静态的社会性构想”和“社会关联先于行动者存在”的批判针对的正是上述问题。区别于卡斯特对信息网络的关注,本文强调作为行动者(actants)的物质身体连接技术网络的过程,我们称之为网络化(networked),而不仅是卡斯特所说的静态的网络(network)。网络化身体影响和参与网络的物质基础构建,也包括人变成信息,媒介信息反向掣肘接入网络的个人身体。在这个意义上,网络化身体中的网络是流动的。作为数据生产者的身体可以接入网络,作为物质的身体又可以逃逸网络,它不断地与其他行动者建立新的连接,网络是行动者实践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最后,网络化身体的概念既带有物质性的视角,也有后人类主义的视角。这个概念将麦克卢汉的经典论断颠倒为“人是媒介的延伸”并不是简单地否定人的能动性,而是从身体物质性的角度重新理解人与技术的关系。人并不是一个异质于技术的存在,其作为物质的身体本身就蕴含着社会与技术网络联为一体的潜能或可供性。我们的身体技艺正是在社会的需求下,在技术的驯化下逐渐发展。在本文所分析的代购、外卖骑手那里都有着明显体现。当然,我们也能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发现端倪。
这种放弃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提醒我们在技术面前放弃骄傲自负与简单乐观的情绪,重新审视技术对人的异化甚至替代性消灭。从当前来看,“网络化身体”伴随的实践在现代技术和制度运转失灵和自我修复过程中确实展现了技术逻辑运转的一体两面。身体和互联网技术的补充与矛盾以后还会在很多类似的情况下以其他方式体现出来。一些技术区隔、制度区隔以及社会关系的空缺会成为“病毒”和“补丁”的滋生土壤。机器性能高速更迭也会加快机器消减“人肉”的过程。中国人工成本的不高和住宅的非标准化会推迟技术系统自我修复和一体化的过程。而无论是正反哪个方向,技术系统的强化都可能加剧涉及其中的某个环节的社会不平等(Xie,2019)。如果缺乏核心价值观,互联网技术的功能性修复和分化便会使人变成“补丁”和“病毒”,现实版的《黑客帝国》(Matrix)[4]正在向人类社会迫近……![]()
本文经作者授权转载自《新闻大学》2021年第5期(总第181期)。
[1] The Government of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Customs and Exercise Department. (2018). Control PointsPassenger Throughput. Retrieved from https://www.customs.gov.hk/sc/statistics/index.html,20190701。
[2] 赖佑萱.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2020年9月8日) [EB/OL]. https://mp.weixin.qq.com/s/Mes1RqIOdp48CMw4pXTwXw,202103 22。
[3] 人民网-港澳频道.香港警方:1614名警察及家属遭非法”起底”和骚扰?(2019年08月23日)[EB/OL]. http://hm.people.com.cn/n1/2019/0823/c42272-31313064.html,20210322。
[4] 《黑客帝国》讲述在名为“矩阵”的人工智能系统掌控现实世界后,主角尼奥等作为入侵电脑的“病毒”与“矩阵”对抗的故事。
[1] [阿根廷]豪·路·博尔赫斯著,王永年,陈众议等译.博尔赫斯文集[M].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
[2] Latour, B.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3] Law, J. “After ANT: Complexity, Naming and Topology.” Actor Network Theory and After. Eds. Law, J., and Hassard, J.Oxford, United Kingdom: Blackwel, 1999:1-14.
[4] [美]约翰·杜海姆·彼得斯,邓建国译.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
[5] 刘海龙.传播中的身体问题与传播研究的未来[J].国际新闻界,2018(2),第37-46页.
[6] [美]南希·K.拜厄姆著,董晨宇,唐悦哲译.交往在云端:数字时代的人际关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7] 孙玮.交流者的身体:传播与在场——意识主体、身体—主体、智能主体的演变[J].国际新闻界,2018(12),第83-103页.
[8] 孙玮.传播再造身体[J].新闻与写作,2020(11),第7-13页.
[9] 芮必峰,孙爽.从离身到具身——媒介技术的生存论转向[J].国际新闻界,2020(5),第7-17页.
[10] 杜丹.共生、转译与交互:探索媒介物的中介化[J].国际新闻界,2020(5),第18-34页.
[11] [美]唐·伊德, 韩连庆译.技术与生活世界:从伊甸园到尘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2]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55周年增订本)[M].北京:译林出版社,2019.
[13] [美]欧文·戈夫曼著,何道宽译.公共场所的行为:聚会的社会组织[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14] [法]马塞尔·毛斯著,佘碧平译.社会学与人类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15] [法]米歇尔·福柯著,杨远婴,刘北成译.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16] [德]诺贝特·埃利亚斯,王佩莉译.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发生和心理发生的研究(第一卷):西方国家世俗上层行为的变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17]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高振华,李思宇译.实践理论大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18] [法]莫里斯·梅洛-庞蒂著,姜志辉译.知觉现象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19] [德]瓦尔特·本雅明,刘北成译.巴黎,19世纪的首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0] [意]维柯著,朱光潜译.新科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21] [美]乔治·莱考夫,马克·约翰逊著,李葆嘉,孙晓霞等译.肉身哲学:亲身心智及其向西方思想的挑战[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2018.
[22] [美]约翰·杜海姆·彼得斯,邓建国译.奇云:媒介即存有[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
[23] Hine, C. Ethnography for the Internet. Embedded, Embodied and Everyday. London and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 2015.
[24] Farman, J. Mobile Interface Theory: Embodied Space and Locative Media. London: Routledge, 2012.
[25] Sheller, M., and de Souza e Silva, A. Mobility and Locative Media: Mobile Communication in Hybrid Spaces. London:Routledge, 2014.
[26] Callon, M. “Some Elements of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Domestication of the Scallops and the Fishermen of St. Brieuc Bay BT.”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32.1 (1984):196-233.
[27] 吴莹,卢雨霞,陈家建,王一鸽.跟随行动者重组社会——读拉图尔的《重组社会:行动者网络理论》[J].社会学研究,2018(2),第218-234页.
[28] Latour, B.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29] 戴宇辰.“旧相识”和“新重逢”:行动者网络理论与媒介(化)研究的未来——一个理论史视角[J].国际新闻界,2019(4),第68-88页.
[30] [美]尤金·W.霍兰德.导读德勒兹与加塔利《千高原》[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
[31] Deleuze, G., and Guattari, F. A Thousand Plateau: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1987/2016.
[32] Deleuze, G., and Guattari, F. Anti-Oedipus: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London: Penguin Books, 1977/2009.
[33] Xie, Z. Brokerage Practices and the Brokers’ Mobilities:The Nexus of Gender, Technology, and Labor in Chinese Daigou.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9.
[34] 束开荣.送外卖:传播实践的物质网络及其时空秩序[D].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论文,2021.
[35] Srnicek, N. Platform Capitalism. John Wiley & Sons, 2017.
[36] 彭兰. 连接与反连接:互联网法则的摇摆[J].国际新闻界,2019(2),第20-37页.
[37] [法]吉尔·德勒兹著,刘汉全译.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德勒兹访谈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38] [美]格拉汉姆·哈曼著,黄芙蓉译.铃与哨:更思辨的实在论[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39] [德]韩炳哲著,关玉红译.精神政治学:新自由主义与新权力技术[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40] [德]马丁·海德格尔著,赵卫国译.物的追问[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
[41] Mol, A. The Body Multiple: Ontology in Medical Practice. North Carolina: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3.
[42] Csordas, T. “Cultural Phenomenology: Embodiment:Agency, Sexual Difference, and Illness.” A Companion to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Body and Embodiment. Ed. Mascia-Lees, F. Chicester:Wiley-Blackwell, 2011:137-156.
[43] [法]米歇尔·福柯著,莫伟民,赵伟译.生命政治的诞生:法兰西学院演讲系列(1978-1979)[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44] [西]曼纽尔·卡斯特著,夏铸九,王志弘等译.网络社会的崛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